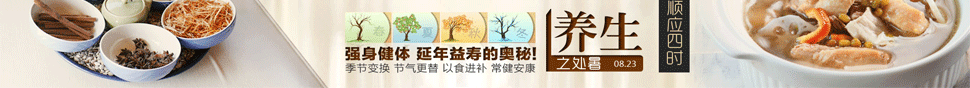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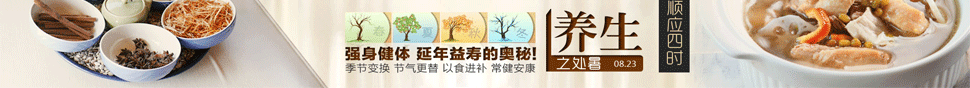
网上有一篇热帖叫《别为我担心,我一个人在大城市很好》,很多人的家人总是问为什么不回来,也许那篇内容里可以给你很好回复。
其实所谓的稳定,是家里人认为的稳定,我为什么不回家做公务员?我为什么不回家稳定安逸?
其实没有为什么,不过离开的那座城市久了,久到觉得那里早就不属于自己。
每一个城市都是一群人的孤单狂欢,我们每个人此生至死,都是孤独的,我们是单独的个体,无论身边出现谁,陪伴谁,最后能陪伴的只有自己。经历过的,擦肩而过的,都是匆匆而过。
那些至死不渝的誓言,那些天长地久的承诺,那些以为会一辈子陪在身边的亲人,那些以为会一辈子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爱人,那些以为会一辈子促膝长谈的挚友,那些以为会一辈子不可磨灭的誓言,终究在春风秋雨中一次次的凋落,走了,来了,散了,聚了。
大大的城市,震耳欲聋的车鸣铁轨声,熙来攘往的柏油马路,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,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群,觥筹交错的灯红酒绿,辽阔深邃的无边长空,哪里是终点,哪里是尽头?!
时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,让一切曾经熟悉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陌生,也会让曾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时间的浸染,慢慢的变的有温度。就比如,我爱这座城市,爱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,一动一静,爱这座城市的历史,爱这座城市的温度和人情世故。
这里承载着社会各种阶层的用途,却被各种阶层瓜分到渐渐失去了他原本的模样。
而这座城市的孤单,不再是几百万人类的孤单,而是那些古老文化遗失的孤单……
中国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古老的,但我们却难以找到几株百年老树和几栋百年建筑。在“年轻”的美国,百年老树和百年老宅则常见得多。近年来,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中,无数中国传统民居都被摧枯拉朽,逐渐消失了,一些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民居竟然漂洋过海,被美国人买去,重新落地在异国他乡。
哲学家们说,人是精神的容器。当我们毁灭真正的城市,然后建起一座座“伪城市”时,城市越来越像一个低效率的生产容器,而非生活容器。
我们的城市就像一辆高速滑行的火车,对大多数普通的城市居民而言,这个溢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,越来越与他们无关。
正如梭罗所说,“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”,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被城市抛弃的绝望与愤怒。他们与城市原有的记忆一起,像一节节被甩下的破旧车厢一般遗落在路边,只能看着城市的车头呼啸而去。这种景象时刻在提醒我们,上紧发条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,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。
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挟裹进社会潮流之中,拥有的物质越来越多,生活越来越丰富,娱乐越来越离谱,心灵却日益疲惫,强烈的郁闷和身份的焦虑却如潮水般袭来。
塞缪尔·斯迈尔斯说:“一个国家的前途,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,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,也不取决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,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。”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,灵魂已跟不上我们的步伐。我们只希望能在这失控的城市更新运动中,给未来的城市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自由生长空间,为我们的后代留有余地;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真正享受一下温暖而惬意的都市生活;让我们在这座城市里,找到一处安宁所在。
可是在焚琴烹鹤、利令智昏的当下,毁灭珍(真)品再造赝品的荒诞悲剧不断上演,许多城市有价值的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,躲过了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乱,却最终逃不脱被开发商的推土机碾得粉碎的命运。在发展就是一切的狂热下,所谓文化遗产,根本无力抵抗商业利益的侵袭。
对当下的中国城市来说,空间的定义、形态和功能只服从于金钱和权力,城市的生活居住功能已经被完全边缘化。交通拥堵、空气污染、被焚琴烹鹤的古宅文物、被一次次开膛破肚的马路、失控的填海填湖毁灭绿地、不断加大的距离、稀少而不当的公共设施、割裂的城市空间,这些都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建设中最具煽情色彩的景观。
但是在法国,奥斯曼以后,法国重新回到民主共和时代,巴黎开始了一轮新的城市更新运动,他们在这场城市拆迁和改造中,特别重视城市穷人的权利,政府不仅不能强行驱赶穷人,反而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为穷人提供服务。法国先后在巴黎周边如伊夫里、苏瓦希、楠泰尔等地,为穷人建设了大量的福利房。他们在80年代以后建设的第三代福利房,基本都是低楼层、低建筑密度,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。
事实上,世界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居住在公共福利房中。人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,房子只是承载人一段生活的车厢。人们不停地上车或者下车,不变的是列车。
相比人的寿命来说,建筑的寿命要长得多,因此可以长期使用。正如果戈理所说:建筑是世界的年鉴,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,它还依旧诉说。在巴黎,拆一幢屋比建一幢房要难得多。但是在中国,拆房只需推土机轻松的扬起和落下,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法国人觉得难于上青天的事情。
而中国这座城市,正在上演一场真正的文化落寞的孤单……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